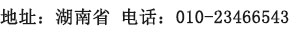“中医不传之秘在于药量”,有的中药疗效不突出或者不够确切,剂量偏低是其重要原因。
中药药典和教科书中,中药用量一般是6-9g或5-15g,不同中药用量通常只有1-3倍的差异。大多在5-15g剂量范围内,频率最高的为10g,没有中间数字的其他剂量,这种用量给人感觉是大多数中药的有效剂量是近同的。
同一中药不同品种、不同产地来源的药效成分含量相差很大,但其用量规定却未有区别。
而经典中,中药用量动则二两、四两、半斤,合今日则为30g、60g、g左右,如补阳还五汤、当归补血汤黄芪用量均达60g,小承气汤大黄用量可达g,《小品方》中以单味川芎治疗妇人崩漏,每日剂量用到.36g《伤寒论》中白虎汤中石膏用量达g,明显是属于超大剂量应用,但每能收到奇效。故我们在处方遣药时应尽可能地“味少而剂重”方可“药专而力宏”而一击中的。
戴复庵在《证治要诀》提出,“药病须要适当,假使病大而汤小,则邪气少屈,而药力已乏,欲不复治,其可得乎?犹以一杯之水,救一车一薪,竟不得灭,是谓不及”。
今医者很少用到此量,在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,也不敢用到此量。医生畏首畏尾,何谈疗效。
当然,现今的药材多是人工栽培,药效同天然、野生药材也有较大区别,今人体质同古人体质也有差别另外,这同我们辨证不够精准,胸无成竹也有极大关系,笔者在临床工作中对此深有同感。
曾治一痹证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甲,女性,45岁,3年前曾在笔者门诊诊治过,近半月来因劳累复发,症见面色皓白,形寒畏冷,易倦思睡,不思饮食,双手、腕、踝、足肿胀、麻木、疼痛,晨僵明显,活动受限,舌质淡苔薄,脉濡弱。
《素问·痹论》云:风、寒、湿三气杂至,合而为痹。考虑该患者体质稍弱,过度劳累,感寒受冷,复发痹证,治以祛风散寒,除湿止痛。方选羌活胜湿汤合乌头汤加减。5剂服后患者诉汗多、畏冷、麻木、疼痛症状基本消失,惟仍易倦思睡,手、足肿胀不退,仍有晨僵,考虑患者痹证复发日久,久病入络,按朱良春先生多用虫类药搜风剔络止痛之意,加用山甲、全蝎、蜈蚣吞服,效仍不显;虑方、证、药无误,苦思不得其解。忽顿悟该患者体质稍弱,久病休息活动少,加之发汗祛湿,必是气虚,急将方中黄芪由15g加至30g,剂后有所好转,将黄芪又加至50g,5剂后诸症大减,再服半月竟建全功。再配药酒日三饮善后,嘱适度锻炼,随访至今未复发。
又治一肝脓肿患者乙,男,72岁,3年前,因胆总管下端结石而行切开取石术,手术及术后恢复均顺利。一周前,突上腹痛、发热,在外地检查后提示肝脏占位、肝脓肿,病灶直径约7cm。予抗炎治疗效果不佳而回本地治疗。医院超检查仍提示肝脏占位、肝脓肿,患者拒绝手术,拟在本院姑息治疗。告知行肝脏穿刺抽脓创伤、痛苦并不大,仍然拒绝。即予头孢等静脉点滴,同时予中药肝脓疡汤加减煎服,方取龙胆草、金银花、板蓝根、苦参、蒲公英、茵陈各15g,连翘、柴胡、山甲珠、黄琴各9g,桅子、赤芍、玄胡索各10g,生甘草9g,水煎服,1剂/d,分3-4次服。5剂后热减退,27.4摄氏度,上腹痛减轻,但复查B超病灶仍未见缩小,笔者胆怯,请教老师,告知病情,越方证无误,可能功力未到,再服5剂,仍未建功,思之再三,考虑药量欠缺,即将龙胆草、金银花、苦参各加至50g,蒲公英、菌陈各加至30g,患者诉药苦难进,嘱冰糖含口中服药,剂后复查病灶缩小,己然建功,再服10剂病灶病灶缩小明显,减少药量调养个1个月后复查病灶消失。随访至今未复发。
故笔者认为,中医药治疗疾病,药量确实是极其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。当然,不能一味认为增大剂量可以加强疗效,就忽视了小剂量药物的作用,形成滥用大剂量的倾向,以图标新立异,增加病人负担,还会对机体造成损害。因轻可去实,四两拨千斤。正如戴复庵所说:“二者(太过与不及)之论,唯中而己,过与不及,皆为偏废”。
精通药性,灵活施用:每味中药有多种功用,某些中药因其用量不同则功用不同,在临床上可根据不同的病证施用不同的剂量。如柴胡用大量在15g以上能疏散退热治少阳病,中量6~10g疏肝解郁,行气化滞,小量3~6g升阳举陷治疗中气下陷。
要加强对中医经典古籍的学习,不断提高中医人员的临床诊疗水平,做到辨证准确,胸有成竹,用药精当,药证相符,疗效迅捷、可靠。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